邬逸聪是谁?谁有邬逸聪资料?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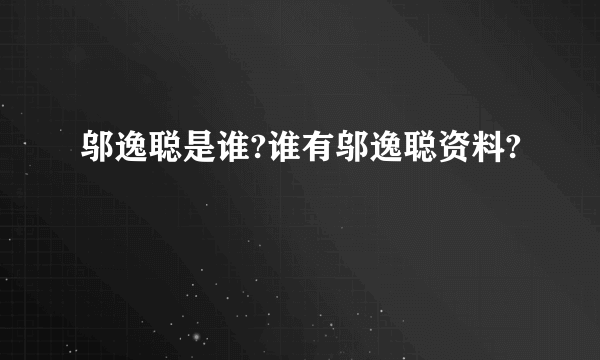
邬逸聪就是邬桑(非成勿扰)。他是一个在日本生活了20年的上海人,是冯小刚多年的好朋友,是将中国电影推销到日本的重要推手,也是《非诚勿扰》的日方制片人,算起来,是一个资深电影人。近日,记者通过越洋电话采访了身在日本的邬桑,并邀请邬桑的老友姜斯轶为其撰文。电话那头,邬桑侃侃而谈,爽朗风趣;友人笔下,邬桑生动丰富,严苛认真———通过这篇报道,您可能会感受到一个比电影更加完整、更加丰满的邬桑。A邬桑何许人中国电影在日本的重要推手朋友印象:脑袋像青春期的刺猬我与“邬桑”头次见面,应是2007年10月下旬,地点在北京,同时会面的还有日本松竹电影公司的几位头面人物。与日方几位一见面,全都是整齐划一的西服领带,只有这个邬先生与众不同:休闲款的外套、休闲裤,穿着越野专用的大头登山鞋,鞋带几乎要一直绑到小腿上;剃成“毛寸”的短发打满了摩丝,一绺绺精神地立着,有些像青春期的刺猬。———姜斯轶邬桑自述:为40多部中国电影做过后期我是上海人,本名叫邬逸聪,娶了一个日本太太,有两个孩子,侨居日本二十多年,已入了日本国籍,有个日本名字叫“宇崎逸聪”,拥有自己的公司,主业是为中国电影在日本做后期制作和海外发行。我1988年来日本,出国前是一个制药厂的工人,到日本后学习的是医药专业。刚去日本,就是典型的留学生的日子,洗盘子,建筑工地,送报什么的,苦活累活都干过。后来实在没钱了,交不起学费,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就去一家电影公司,那份工作是深夜拷贝录像带。后来别人觉得我还不错,正好那家公司在做中国电影的后期,缺翻译,就让我做中国电影的后期制作的翻译。电影这个东西我以前就很感兴趣,我对摄影啊什么的都熟悉,所以一下子就学上手了。除开最初的两年,我在日本的20年中有18年都是在做中国电影,主要在做后期的技术工作,和胶片打交道,音乐画面都负责。在日本,当年做这个行业的中国人就我一个。我做过的电影不少,当时很多片子,只要是在日本做后期的,基本上我都参与过,有40多部吧,包括《霸王别姬》《风月》《活着》《阳光灿烂的日子》《太阳照常升起》。大概六七年前,我被另外一家公司挖走,开始做中国电影在日本的发行,先后做了大概40多部吧,包括《英雄》(看专业剧评)《十面埋伏》《无极》《霍元甲》,我还做过一些技术上的制片,包括《孔雀》和《暖》。《天下无贼》我也参与了后期和发行。B半部《非诚勿扰》他和冯小刚聊出来的朋友印象:他结巴,说的都是心里话邬桑是个不大善于言辞的随和人。我虽然觉得他长相如同金刚,但当看到他搂着孩子亲亲抱抱的时候,又觉得百炼的精钢一下子变成百转千回的绕指柔肠。邬桑的不善言辞,最典型的莫过于《非诚勿扰》全球首映礼当天,当主创团队上台与观众见面时,邬桑过于激动,一句话被结结巴巴地反复了好几回。现场观众也受了感染,对他结巴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大家可能都明白,虽然他讲话结巴,但结巴的即兴讲话往往是心底的实话。———姜斯轶邬桑自述:小刚一到日本就跟我喝酒小刚当初写邬桑这个角色的时候就说“别改了,就是你”。邬桑就是我,只不过我没有生活在北海道,不是农民。我和冯小刚是多年的朋友,我们都是一个圈子里的人,我跟张黎熟,他是《天下无贼》的摄影,当时这片子要来日本做后期,就是张黎联系的,我和小刚就熟了。做完《天下无贼》,他每次来日本就找我喝酒,他年龄比我大一岁,我们是同龄人,很投缘。小刚来日本宣传《夜宴》,当时恰好还有时间,小刚就说一起去北海道吧。我就跟他说,去知床吧。我开着车,小刚和他的助理,我们三个大男人在北海道逛了4天。我们当时的路线,和这次《非诚勿扰》的路线一模一样,只不过当时是冬天,下着雪,我们拍的时候是秋天。小刚这人一上车就不睡觉,一路上我们就聊。他问题特别多,电影里的很多东西都是当时聊出来的。比如小刚老看到那种带尖顶的小房子,就问我是干嘛的,我说是用来忏悔的小教堂。小刚说自己要去忏悔,他的助手张述跟他说,那教堂太小了,你的罪恶太多,这里装不下,你得找个大的。电影中的葬礼、教堂、吃海鲜烧烤、还有四姐妹居酒屋,都是当时聊天聊出来的,当时没有想到要专门为一部电影聊点什么,就是男人之间的瞎聊。但是小刚这人脑子特别好使,他都给记下来了。当时小刚就说,这里太美了,得来弄一个电影。我当时认为他这想法很不靠谱。后来他突然说要拍了,我就给他弄了很多资料,日本的风土人情,题材什么的。我是这部电影日方的制片人,是在日本拍摄部分的总负责人。C首次当演员是为了哥们儿上贼船朋友印象:严谨,苛刻,“可怕”别看邬桑演着喜剧,只要和他共事过,就知道他对工作的严谨已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往往让其他人感到此人相当“可怕”。在各大门户网站的《非诚勿扰》专题里,也许是因为找不到任何与“邬逸聪”有关的资料吧,他的名字竟在客串名单中被直接删除,这种擅自删除他人署名的做法,显然并不尊重他人的劳动。———姜斯轶邬桑自述:忏悔那场戏小刚发火了4月我们去看景的时候还没说让我演,后来要拍的时候突然说要我来演。我推了,但没推掉,因为角色都照我来写的。我不是演员,没有自信,压力特别大,那三个月,我一边做制片,一边演戏,后悔死了,我宁可只做幕后。我的感觉就是“上了贼船”,拍了第一天就想下来,但没人能替我,我不拍就是对不起哥们儿。第一场戏,我一边开车,一边说“日本人肯定以为我们中国人特仗义”,就是那一段车里的戏。我觉得怎么说都没有京味儿,说不出来,大概拍了四五条才过。我看剧本只知道看自己的部分,我就划上红线,背得滚瓜烂熟。但一到镜头前就全忘,每次葛优说完,我都不知道是不是该自己接上去。后来小刚说,不行,你把你那剧本扔了,重给我一个没划红线的剧本看。另外,小刚拍戏主张说话自然,我做不好,小刚就说:“你不是没演过戏吗?怎么说话跟话剧台词一样?”我个人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是在教堂忏悔的那段。拍到一半我发现这个角色和我想像得不一样,我那个时候开始对角色有想法了,我觉得我应该特别酷,装酷,装深沉。小刚可能考虑的是整体的画面感觉,他说:你手不对,脚也不对!我老别扭。拍了一条,两条,好多条,他突然嚷嚷:“不拍了,就这么着了!”他一嚷我们大家都急,气氛就紧张起来了,我一看他急我就更紧张了。你说片场那么多人,还有一半是日本人,还听不懂他嚷什么,我也抹不开面子啊。我们私底下在一起都是哥们儿,我叫他小刚,在现场,得叫导演,我就跟他说:“导演,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吧!” 他说行。最后一条才过。有的时候,你在思想上理解了,但手脚跟不上,我就觉得我宁可不挣钱,也不要当演员。我相信这样一句话,你是一头猪,你不会爬树,就不要想着当一头熊。D那场哭戏是哭我在日本的20年朋友印象:细心、火大、易怒邬先生长了一副大庙山门前“护法金刚”的面孔,狮鼻虎目,肤色微黑,颇具有些威慑力。身量并不很高,却很壮健,上肢尤其发达,常作拳击手出拳、闪躲状。我不谙技击,但也能明显听到他出拳时有风声,很有力道。邬先生说话很直接,也最讨厌别人说话吞吐含糊。细心,但不是慢性;火大易怒,但罕见焦躁之态。———姜斯轶邬桑自述:哭戏,我酝酿了好几周那场哭戏,怎么说呢,我拍这场戏,我的整个感觉是很复杂的,基本上就是我在日本的20年的经历、辛酸、所有的心情,都在里面了:他乡遇故交,见面又分手,朋友未知的将来,基本上都是我生活的真实写照,非常复杂。有经历的中年男人都能体会这种情感吧。哭戏是两条过的。那个下午就安排了这一场戏,大家都知道我需要一个人,就没人和我说话。一个副导演说,邬桑你睁眼看太阳,看十秒就能流泪,剧组还给我准备了眼药水。其实没人知道,我为这场戏酝酿了好几周时间,我觉得这是我最重要的一场戏。那首《知床旅情》,我自己很喜欢这首歌,我想我一定能哭得出来。那天拍第一条的时候,小刚坐在车后座。他自己拿着机器,说:“你觉得可以开了,我就开机。” 可是他在我怎么也演不好。他一说:“开吧。”我一点心情都没有,就开着车在路上绕了一圈,突然感觉来了,可是路也走完了。拍第二条的时候,让吕叔(吕乐) 上。吕叔是个绅士,他自己也做导演,他跟我说:“你什么时候都可以,我不和你说话了。”吕乐躺在后座上等我,这一次我顺利过了。后来换机位什么的又拍了四五条,我感觉一发不可收拾,伤心得死去活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