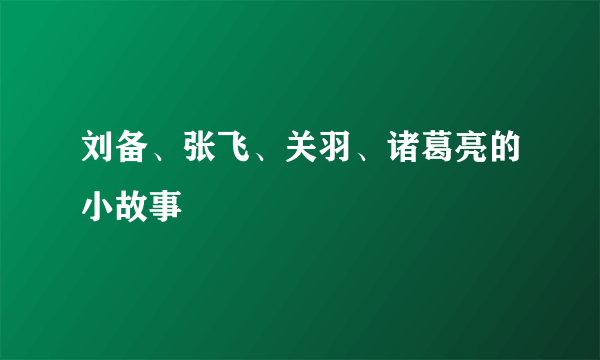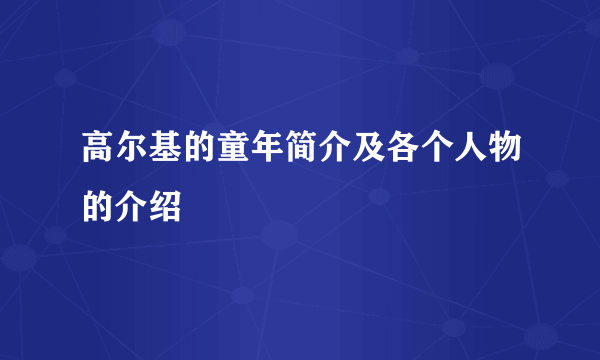《命命鸟》故事简介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
小说品读许地山的作品,无论小说、诗歌还是散文,都以“诗质”见长,正如沈从文所说:“以佛经中邃智明辨笔墨,显示散文的美与光,色香中不缺少诗,落花生为最本质的使散文发展到一个和谐的境界的作者之一……最散文的诗质的是这人的文章。”[1]其中意象的有意设置是一重要因素,这些意象既有丰富的美学内涵,又是他生命哲学的承载体,因此是理解他作品主题和艺术风格的关键。他的前期作品受佛教影响甚深,其成名作《命命鸟》尤为明显。他借鉴了大量佛教意象并加以改造,形成与当时文学主流截然不同的文风,当时就引起文坛许多名家的关注。然而时至今日,评论者们对《命命鸟》的解读,要么研究佛教对该文本的影响,要么放在该篇文体的诗化特征上,却没有进一步探讨主题是如何显现的,以及诗一般的意境由何而来。本篇拟从意象角度对《命命鸟》进行重新解读,阐释这些意象对文本结构、主题和风格的影响,以期更接近《命命鸟》的原初状态。贯穿《命命鸟》始终又使人浑然不觉的意象是“光”。由“日光”经“佛光”至“月光”,是敏明与加陵经历了爱情的萌动、生长、受阻终至寂灭,生命也走到尽头的过程。光的变幻与他们的命运流转密切相关。文章开篇即出现了日光:“早晨底日光射在她脸上,照得她的身体全然变成黄金的颜色。”这日光有着多重涵义。日光从古至今,因其光明普照而成为生机的象征,这里以日光这一意象展开故事也有此意。就在这美好的日光中,敏明与加陵的爱情如春苗般蓬勃滋长,走过青涩,走向成熟。同时,日光又与佛教有极深的渊源,佛经中常用日光来喻佛法,取其日出暗消,普照四方之意,喻佛法无边,可以普度众生。日光与敏明手中的《八大人觉经》搁在一起,显得极有佛教意味。而日光打在敏明身上呈黄金颜色,这“金色光”更是佛教的重要意象。《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第八观云:“佛菩萨像,皆放光明。其光金色。”第十五观云:“见阿弥陀佛与诸眷属,放金色光。”佛光所照之物,受佛光明,也呈金色,如《七佛神咒经一》云:“其中所有一切万物,皆如金色。”又如《大乘无量寿佛庄严经》中说《法华》放光现瑞时:“照于东方万八千土,皆作金色。”这金色光于施者是济度,于受者是受佛接引。日光、《八大人觉经》与日光下敏明身体的黄金颜色组合在一起,暗示着敏明与佛的厚缘及将来的命运,结合下文,这开篇即出现的“日光”意象成为主题呈显不可或缺的一环。随着瑞大光塔的佛光的几次出现,敏明与加陵的爱情也出现了外力的阻挠,敏明对佛显出愈来愈亲和的态势,最终在佛光中开悟,与加陵共赴涅槃。可以说,佛光不但伴随着他们爱情的陡转与寂灭,而且是促使这一系列事件发生的重要契机。瑞大光为仰光佛塔,塔顶祥云缭绕,金光四射。文中提到瑞大光塔的佛光的文字有以下几处,其中前两次,加陵与敏明分别与佛光接触,这里的佛光也为金色:“湖西远远望见瑞大光,那塔的金色光衬着……不论什么人,一到那里,心中的忧郁立刻消灭。”(——加陵)“瑞大光的金光远远地从那里射来”。(——敏明)最后一次提及的佛光是敏明所遇:她定神瞧着围绕瑞大光的彩云,不理会那塔的金光向她的眼睑射来,她精神因此就十分疲乏……她又瞧见上面那些王侯所献底宝石,个个都发出很美丽的光明……那宝石已经掉在地上。她定神瞧着那空儿,要求那宝石掉下底原故,不觉有一种更美丽的宝光从那里射出来。上文已经提及,“金色光”在佛教中是极尊贵的佛光,如《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云:“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遇斯光者,垢灭善生,身意柔软。若在三途极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终皆得解脱。”敏明就是在这金色光中走进幻境,得佛接引,看到自己与加陵的本来面目,找回迷失本性,终至双双投水,完成涅槃的。这佛光意象是故事扭转的关键,无此后来的故事就无法依作者意图发展。“佛光”意象消隐之后,继之而来的是“月光”意象。月光反复出现,陪伴着敏明与加陵完成了他们告别尘世的旅行:“因为那夜底月亮亮得很,敏明和月亮很有缘……。”“那时月光更是明亮。”“在月光水影之中,还听见加陵说:‘咱们是生命底旅客,现在要到那个新世界,实在叫我快乐得很。’”“月光还是照着他们所走底路……。”早在原始时期,人们就感觉到昼夜、日月的更替与万物由生而死的变化过程的相似性。白天世界是人活动的空间,夜晚似乎是鬼魂出没的场所,这种思维与日月的自然属性有关——日光热,月光寒。在文学中,这一意象又衍生出与此相关的多种象征意韵。这里的“月光”意象与敏明与加陵的死相连,又与开篇的“日光”意象遥相照应,暗示一个生命的回环。月光柔和而清凉,带有母性的某些特征,又赋予死回家、回来的感觉,冲淡了死本身的恐怖色彩,而有一种灵魂脱离肉体的束缚,回原来应该在的地方去的浪漫味道,让死变得凄绝美绝。在光的流转中,上演了一对“命命鸟”在尘世的一次从迷失到回归的故事。“命命鸟”是佛经中的一种鸟:“梵语耆婆耆婆迦。法华涅槃经等谓之命命鸟,胜天王般若经谓之生生鸟,杂宝藏经谓之共命鸟,阿弥陀经谓之共命之鸟,乃一身两头之鸟也。” [2] 耆婆耆婆:“鹧鸪之类,由鸣声而名,耆婆为命或生之意,故云共命鸟。”[2] 该鸟和极乐国土上的其他鸟一样,是宣扬法音的:“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白鹤、孔雀、鹦鹉、舍利、迦陵频伽、共命之鸟,是诸众鸟,昼夜六时,出和雅音,其音演畅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如是等法,其土众生,闻是音已,皆悉念佛念法念僧……是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欲令法音宣流,变化所作。”[3]从上可以看出命命鸟是一身两头、不可分离之鸟,且是生命的象征。在极乐国土,命命鸟和其他诸鸟一样,是阿弥陀佛的化身,目的是为了宣扬佛法。许地山把“命命鸟”作为本文的主题意象显然借鉴了佛教中该意象的意蕴。本文中的“命命鸟”显然与佛教有厚缘,他们在尘世为敏明和加陵,时时感到彼此在对方身体之中,不可分离:加陵:“不晓得要写些什么才能叫你觉得我的心常常有你在里头”。敏明:“咱们是同一个身心,/同一副手脚。/我和你永远同在一个身里住着。/我就是你啊,你就是我……你不要象他们这样的眼光。/要知道我就是你啊,你就是我。”加陵:“我也很愿意对你说:我就是你,你就是我。”尘世中的“命命鸟”(也即敏明和加陵)有着彼岸命命鸟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自觉意识,又有不同于彼岸命命鸟的地方,具体表现为贪恋对方,执著尘世,是世俗化的“命命鸟”。幻象中的“命命鸟”与此有同有别:“南边的树枝上有一对很美丽的鸟呆立在那里,丝毫底声音也不从他们底嘴里发出。”作者着重强调了这里的“命命鸟”是一对无语的呆鸟。缘何无语?我们可以理解为因为他们的肉身还在尘世,迷失于俗恋之中,没有回来,所以不能像其他鸟一样宣唱法音。同时作者也通过这一意象来表达他对人与人关系的理解,呆立无语意味着无法对话与沟通,象征着生命个体之间无可消除的隔阂,无论如何相爱也无法真正懂得对方。试想,相爱如敏明和加陵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俗人呢?结合故事情节,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如对宗教,敏明是用情感去信仰,加陵是用理性去评说,故加陵非难佛经中关于秽净的观点敏明颇不赞同。对于爱情,敏明比加陵更看重灵的契合,这就有了加陵想得到敏明的吻,敏明却“好象不曾听见”。最有趣味的是,他们连自杀也不是基于同样的原因,敏明是通过幻象看破世事而情愿弃绝尘世,“转生极乐国土”。加陵却是因为“未到过那城,所以愿意去瞧一瞧”,加之离不开敏明。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借鉴佛教中的“命命鸟”意象的同时又赋予这一意象更多的意蕴,这里的“命命鸟”还象征着人与人之间与生俱来、无处不在的的隔膜,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爱情的独特理解,认为这种状态已经是爱情的最好境界了。爱的欲望使人渴望身心交融,隔膜却使人无言相向。爱与隔膜的冲突通过这一意象刻画得既富有诗情画意又如此的刻骨铭心。何以如此呢?看看“彼岸”(注:幻象中的“彼岸”是以极乐国土为“此岸”而言的对岸,实指尘世)的“命命鸟”们就明白了。幻象中另一岸的命命鸟们则更为不堪,他们立在“情尘”的花瓣雨中,相互对一切异性说着相同的情话,继而翻脸无情,甚至互相啮食,和这对无语的呆鸟根本不能相提并论。许地山就这样通过“命命鸟”的不同状态表达了他对人生、爱情的认识,把一个普通的爱情悲剧上升到探讨人生本相的高度,主题也不仅仅是演绎个体爱情的悲欢,而是浸染着浓厚佛教气息的独特的生命哲学。命命鸟本从极乐世界而来,当然应回极乐世界中去。从这一理解出发,我们方能理解结尾处许地山描述他们之死时隐隐的喜悦,因为从佛教的角度看,“死”只是两只命命鸟迷途知返,重新回到原来的世界罢了。在幻象世界中,围绕着“命命鸟”这一意象的还有很多意象,和“命命鸟”一起组成了一个和谐的意象群落。其中“此岸”(也即佛教中的极乐世界)由种种美好事物组成,与佛教净土宗所宣扬的弥陀佛极乐世界极为相似:“两边的树罗列成行,开着很好看的花。红的、白的、紫的、黄的,各色齐备。树上有些鸟声,唱得很好听。走路时,有些微风慢慢吹来,吹得各色的花瓣纷纷掉下:有些落在人的身上;有些落在地上;有些还在空中飞来飞去。”“……有些泉水穿林而流。水面浮着奇异的花草,还有好些水鸟在那里游泳。”佛教中的极乐世界是这样的:“风吹散华,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泽,馨香芬烈,足履其上,陷下四寸,随举足已,还复如故。……,随其时节,风吹散华,如是六反。又众宝莲华,周满世界,一一宝华,百千亿叶……一一华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无量寿经》)“如意珠玉……其光华为百宝色鸟,和鸣哀雅,常赞念佛念法念僧。” [4]“一一池水,七宝所成……其摩尼水,流注华间,寻树上下,其声微妙。” [5]两相对比,可以看出,这幻象世界几乎是佛经故事中极乐世界的再现。书中的视觉意象、听觉意象、嗅觉意象皆来自佛经,在佛教中这些色、声、香与味、触、法合为“六尘”,在极乐国土,因为为佛所化,一一圆明具德,故见光、见树、闻声、嗅香,莫不增益善根。所以有缘人若“目睹其色,鼻知其香,口尝其味,身触其光,心以法缘,皆得甚深法忍,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六根清澈,无诸恼患。”[6]然而即使是这样的色声香与佛法相比也粗劣的。正如“那人”对贪恋于此的敏明所说:“你只会听粗陋的声音,看简略的颜色和闻污劣的香味。那更好的、更微妙的,你就不理会了。”与佛教极乐世界所不同的,是在本文中这一切作为命命鸟活动的背景而存在,同时还设置了一个与此相反相对的“彼岸”世界。这里试以花意象和流水意象为例,具体作一分析。这个世界也有花,却是“情尘”[7],这“情尘”对葬身其中的“命命鸟”们不但无宜,反而有害:其一表现为使人感情反复无常,其二则更等而下之——使人互相残害啮食。同为花,却对人或宜或害,很不一样。为何?也与佛教有关。因为佛教认为尘世中的花为色,属“六尘”,使人迷失原来智性的原因之一,所以称花为“情尘”,迷失其中将害人害己。而极乐国土上的所有生物都是佛的化身,自然与此不同。敏明在两种花的截然不同中,看到人世间感情的无常,懂得人生痛苦的真谛,完成了思想的转变。本文中的流水意象也是富有多重意蕴的自然意象。流水作为生命之源,由此衍生出复活与再生的功能,同时水可以洗濯万物,包括自身,所以又被引申为可以洁净灵魂之物。因而“水的再生功能,就较直接地渗透到丧葬、成年 、嫁娶与诞生这四大人生礼仪中……中国自古文人多水死。许多列女也以自溺求得灵魂洁净”[8],P.E.威尔赖特曾解释洗礼的意义说:“来自于它的复活的特性:水既是洁净的媒介,又是生命的维持者。因为水既象征着纯洁又象征着新生命。” [8]《尸子》曰:“水有四德:沐浴群生,通流万物,仁也;扬清激浊,荡去滓秽,义也;柔而难犯,弱而能胜,勇也;导江疏河,恶盈流谦,智也。”[8]水的这些意蕴为佛教所利用改造,成为富有八种妙用之物。《称赞净土经》云:“何等名为八功德水?一者澄净,二者清冷,三者甘美,四者清软,五者润泽,六者安和,七者饮时除饥渴等五两过患,八者饮已定能长养诸根四大,增益种种殊胜善根。多福众生,长乐受用。”《佛说无量寿经》认为,水“开神悦体,荡除心垢,清明澄洁,净若无形。”在本文中,流水意象显然沿用了水的这些功用。文中最先出现的水意象是绿绮湖:“绿绮湖是仰光第一大、第一好的公园……不论什么人,一到那里,心中的忧郁立刻消灭。”这里的水虽然是尘世中的水,但在常人眼里,自然是让人舒服愉快的。接下来出现的水意象是幻象中的泉池,伴随着好听的乐音,这水与前水不同,因受佛光明而具佛性,自然发乐音,是开释众生之物,因此接引人借此来点化敏明。结尾处的水是敏明与加陵去往极乐国土的媒介,与涅槃节、月光、优钵昙花等意象放在一起,带有极浓的神圣意味,是再生与洁净的统一体,这里所谓再生指的是永不生不死的状态,洁净是洗去滚滚红尘中所沾染的种种污垢,现出原来具足的本性,许地山安排敏明和加陵投水而死,显然也是受佛教文学的影响。以上种种意象与文中的诸如芒鞋、孔雀翎等有着异域情调和佛教色彩的其他意象聚集在一起,构成了小说柔和、宁静的叙述笔调和凄婉而不哀伤、甚而有些淡淡的喜悦的整体氛围,同时参与文章的叙事,共同形成一种“圆圈”式的叙事结构,并丰富了小说的主题,使小说有了多种阐释可能性。因为这些意象的存在,这篇小说就不单单是一对痴情男女在封建家长制的压迫下以死抗争,成为封建制度的牺牲品的故事,也可以看成是极乐国土的一对命命鸟堕入凡尘,由贪恋对方到其中一只于幻境中开悟,双双涅槃,回归原来所在乐土的过程。其主题除了揭露封建制度的压制人性与歌颂美好纯真爱情之外,更在幻象和现实的对比中,探讨了生命的悲剧本质,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冷漠,世事情感的反复无常等,从这一点看,这篇小说又是一则带有浓厚佛教文化色彩的人生寓言,是许地山独特的生命哲学的载体。从文学传承方面看,文本中的这些意象对古典美学意象尤其是佛教意象有明显的借鉴之处,其中一部分直接取自佛经,如命命鸟、佛光、优钵昙花等,有些自然意象如花草意象、流水意象,其意蕴也深受佛教影响。如此大量地在小说中运用这些意象,建构成神秘奇幻的意境,在20世纪20年代文坛上是罕见的,这也许是许地山小说一打上文坛就引起极大关注的原因之一。然而毋庸讳言,这份新奇终究是建立在借鉴之上的,即使有所改造,总免不了给人似曾相识之感,可以说既是特点又是局限。探讨《命命鸟》一文的意象,也是为了更好地研究许地山作品特别是早期作品的艺术特点和主题内涵。[1] 作者简介许地山现代作家、学者。出生于台湾一个爱国志士的家庭。1917年考入燕京大学文学院,1920年毕业留校任教。期间与瞿秋白、郑振铎等人联合主办《新社会》旬刊,积极宣传革命。“五·四”前后从事文学活动,后转入英国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学院研究宗教学、印度哲学、梵文等。1935年应聘为香港大学文学院主任教授,遂举家迁往香港。在港期间曾兼任香港中英文化协会主席。一生著作颇多,有《空山灵雨》、《缀网劳蛛》等。现在徐闻县有他的故居。许地山[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