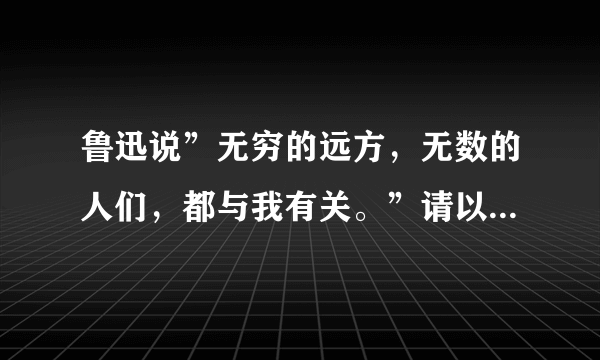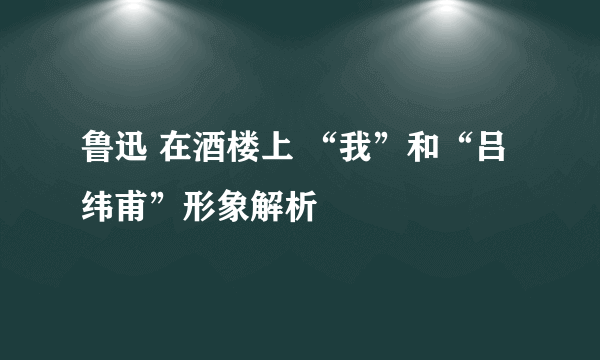鲁迅为什么诅咒长城?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
献给长城的赞美诗是不计其数的,唯独鲁迅曾在20世纪初别出心裁地评价:“……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尝挡得住。现在不过一种古迹了,但一时也不会灭尽,或者还要保存它。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连为一体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何时才不给长城添新砖呢?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 长城该诅咒还是该赞美? 北京啊北京,北面有长城,东面有运河,这是两座足以概括其历史的无字的纪念碑,而南面则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这使它获得了一般城市无法比拟的鲜明的地理特征。在我意念中,运河是母性,平原是父性的,逶迤于北部中国额际的长城像一道风化的皱纹,则是屏障般的群山之子,挥洒着永葆童贞的男儿血性。献给长城的赞美诗是不计其数的,唯独鲁迅曾在20世纪初别出心裁地评价:“……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尝挡得住。现在不过一种古迹了,但一时也不会灭尽,或者还要保存它。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连为一体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何时才不给长城添新砖呢?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 他对长城实用价值的怀疑并未真的影响到长城在今天,在一个和平的年代的审美价值。凡是来过北京的人,几乎没有谁不去看长城的。长城是北京最著名的邻居。它甚至比这座城市还要古老。人们仍然在忙于修补长城,不是为了防御战乱,而仅仅为了纪念。长城曾经保护过我们,现在到了该我们保护长城的时候。它的箭垛、阶梯、烽火台如同岁月的蛀齿,几乎每隔几年就要修补一次。否则在风吹雨淋的日子,古老的中国会牙疼的。又怎能不给长城添砖呢,包括我这篇文章,都是献给长城的众多赞美诗中最新一首。 每天都有从世界各地通来的游客,站在粉饰一新的长城上摄影留念,这是和中国的几千年文明合影的最佳位置。凸凹不平的每一块城砖上面,重叠着多少代人的脚印,或者说,浓缩着中国的往事。从这个角度来看,长城已被神化了。是整个民族的精神寄托,象征着对历史的崇拜与信仰。无法想象,长城会有倒塌的一天,又有谁的手能将它从地图上抹去?它称得上是中国的第一号文物了,享有着至高无尚的尊重与保护,像一位活在我们周围同时又活在民族记忆里的沉默的老人。长城的影响是穿透时空的。 也许每位中国人都会像鲁迅那样,“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不管你是感到安全抑或制约。这或许就是传统吧。在长城脚上生活,在传统的影响下顺从或者叛逆,彷徨或者呐喊,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命运。 北京是离长城最近的一座城市,也是受传统的影响最深远的城市,所以它成为中国历史上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朝代的首都。鼎立于长城脚下,但它不是传统文化盲目的顺民,亦有着自身的思辨与判断,对传统进行着消化抑或抵触。所以北京也是历朝历代政治气氛最浓郁、思想斗争最激烈的一座个性化城市,尤其近代以来表现得愈加明显。 譬如,鲁迅对长城的那段诅咒,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写出的,他一气之下将长城作为封闭、保守、落后于时代的传统文化的替身或象征物而加以批判。实质上长城本身倒是无辜的。 鲁迅还在菜市口的绍兴会馆写出了《呐喊》,隐忍与缄默的长城脚下,终于出现了充满反叛意识的呐喊之子。呐喊的声音在北京城的上空回荡着,历史并未感到陌生,鲁迅并不是第一个、更不是最后一个呐喊者与叛逆者。绵延且郁积了几千年的传统的建设者是伟大的,但其破坏者同样是富于勇气的,正好长城刀光剑影的传记,恰恰是长城内外固执的守卫者与不懈的进攻者共同写下的。或者说,他们共同创造了历史。我读过某外国历史学家的《尼罗河传》,当时就想到,应该有一部《长城传》,它足以包容中国最漫长的封建时代之始终。长城是当之无愧的传主。或许这部《长城传》本身存在着,以无字天书的形式,陈列于北部中国的青玉案上。别人可以为一条河流作传,但你能说长城不是一条横跨民族历史的凝固的河流吗? 这就是我来到北京后的思考。这就是我对长城复杂的感情。多年前流行过电视剧《霍元甲》主题歌“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将长城与黄河皆作为中国人的精神支柱相比拟。黄河是民族的摇篮,是造物主呈献给它的子民的一份厚礼;长城则是中国人亲手缔造的一个神话。前者出自天意,后者出自人为,甚至今人对长城的维护都堪称一项修补神话的工程。 很少有谁敢于怀疑长城的不朽,除了鲁迅曾为抗议黑暗的世纪而选择过那偏激的立论。鲁迅是有勇气的。但不管怎么说,长城的意义远远超越了它最初的建造者的想象,尤其在闭关锁国的封建时代结束之后,它的防御功能早已退化了。长城所记载的那些胜利抑或失败,都已构成历史,它在现代社会最大的价值就是能够提供遥远的见证。长城是中华民族历史古老的证人,沉默的证人。它的存在就是证明。 和长城相比,运河则寂寞得多。北京东郊的通州是曾经赫赫有名的京杭大运河的起点(金代开凿潮白河下游,经元、明两朝治理疏浚,方通杭州)。可自从潮白河水断流、航运停止之后,北运河即成为排水河道,主要用于灌溉农田——贯穿了大半个封建时代的千年漕运史,业已随昔日辉煌划上一个黯淡的句号。北运河遗址,是通州城内现存的文物古迹之,使用遗址一词让游客绝望。我来北京后,曾特意驱车出朝阳门去拜访过,发现古运河已成一潭死水,漂满空易拉罐、废纸、朽木与菜叶,看不见轻盈的舟影,更听不见那浪漫的桨声了。北运河已经死了,在做完了温柔富贵梦之后停止呼吸,你简直无法想象它曾拥有过千帆竞渡、百舸争流的繁华场面。甚至斜阳衰草间如我这样虔诚的凭吊者,也寥寥无几。仿佛此情此景不足一游。但要知道,元、明、清直至民国,运河的水路都曾经是南北交通与运输的要道,当时通州是北京城的大粮仓,几乎每天都有整船整船的粮食、丝绸及其它货物自江南水乡远道而来,囤积在码头上。可这一切皆已随社会的发展而灰飞烟灭,如同一个缥缈而原始的梦境。北运河遗址已快成为一个没有风景的风景点了,一个没有游客的名胜古迹。无法挽救了。由此可见,它远远不如长城那么幸运,虽然同样都是历史的证人,一个是战争的产物,一个是和平的化身。运河的繁华曾经忠实记录过一个又一个太平盛世,当然,它那富裕、自由、美满的梦想大多是在长城的呵护下诞生的。 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关系。这就是中国的历史。所以在我的回忆中,长城与运河互为补充,长城不倒,运河不死,它们曾经是漫长的封建时代最重要的命脉。同时也为今人的追怀提供了沉默的证词。北京啊北京,北面有长城,东面有运河,这是两座足以概括其往事的无字的纪念碑。此时此刻,我的双手正在触摸着它们,触摸着它们波痕般的纹理抑或纹理般的波痕,石头是冰凉的,水也是冰凉的,可我却穿透时空测量到那一个古典的中国的体温……